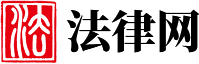绿色生态种植的现实意义野芋
2022-07-20 04:23:18 瑞士农业网
绿色生态种植的现实意义
近日,“国研中心农经部”部长在顶级官媒发表署名文章,阐述“让农业绿起来”的高见,其中最为“精彩”的一段如下:
“近年来关于绿色农业存在不少认识误区,有些甚至流传甚广、影响颇大。例如,只要提到化肥、农药、饲料和添加剂,不少人就会心生反感;只要提到农产品质量安全,不少人就会想到发展有机农业、纯天然农业。在一些舆论宣传、广告推介中,往往把质量安全等同于不用化肥、农药,不喂饲料、添加剂。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提出让农业绿起来、实现农业绿色化发展的新目标,一定要防止走极端,防止一味抵制和排斥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在农业中的应用。让农业绿起来,绝不是要退回到工业文明之前的传统农业。那时的农业当然是绿色、有机的,但靠那种农业怎么可能养活得了今天这么多人口?不用化肥和农药的种植业,不喂饲料和添加剂的养殖业可以少量存在,但难以成为现代农业的主流。对我国几千年农业发展史的研究表明,在使用人力和畜力、耕地不休耕和轮作、靠人畜粪肥维持地力的条件下,要实现氮这一主要营养元素的平衡,粮食亩产只能达到100公斤。这与现代农业能够达到的亩产400公斤相去甚远。”
上面这段文字包含着几个耐人寻味的观点及其错误,容笔者一一道来。
1、基本国情判断尚客观
部长先生说,“不用化肥和农药的种植业,不喂饲料和添加剂的养殖业”养不活中国近14亿人口。这个判断是客观的。笔者在《人口困局》第3章详述了人口恶性膨胀所导致的环境污染、食品污染和食品品质恶化的严重后果:
“问题很清楚,为了解决13.4亿人口‘吃饱’的问题,我们只能大量使用化肥去提高产量,大量使用农药‘虫口夺食’,大量使用动植物激素缩短动植物生长周期,以增加产出批次,大量使用抗生素以尽可能提高畜禽鱼虾的养殖密度,同时,也大量使用农膜掠夺土地肥力,提高高寒高海拔地区的粮食生产能力。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动用其它一切科技手段尽可能地增加食物供给,尽管一些‘高科技’手段的安全性不明,比如转基因食品技术”;“这一切都无法顾及食品污染和环境污染,并且也只能眼睁睁地任由这些污染恶性循环,累积恶化”。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把化肥、农药、动植物激素、抗生素和农膜这五个‘食物减产效应’叠加在一起,即在全国推广‘可持续的绿色生态食品种植养殖模式’,停止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动植物激素、抗生素和农膜,那么,我国生产的食物恐怕连半数国人也养活不了”。
笔者之所以首先肯定部长先生的上述判断,是因为,这个判断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基础。如果无视这个基本国情,就会严重误判中国的未来。
2、误判公众绿色生态环保意识苏醒的历史性意义
30多年来,因为人口总量巨大,我们只能用化肥、农药、激素、抗生素和转基因食品“喂饱”国人,并因此而“喂大”了一代青年及其他们的子女,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渐变,让老中青几代国人都失去了警觉。然而,近些年,随着一系列恶性食品事故的曝光,随着国人被一系列莫名其妙的疾病缠身,随着一个个年轻生命因猝不及防的癌症嘎然而止,人们的绿色生态环保意识终于开始苏醒。这最初被环保先驱者追求的“一缕阳光”很快就唤醒了公众。人们开始追求绿色、生态、环保,开始视化肥、农药、动植物激素为毒物,并且正如部长先生所说的那样,人们开始推崇“有机农业、纯天然农业”,并“流传甚广、影响颇大”。
这无疑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是,很遗憾,部长先生将这一重大进步定义为“关于绿色农业的认识误区”。
3、低级的常识性错误
部长先生之所以把绿色农业看成“认识误区”,缘于他的一个非常低级的常识性错误。他蓄意伪造数据说,“对我国几千年农业发展史的研究表明,在使用人力和畜力、耕地不休耕和轮作、靠人畜粪肥维持地力的条件下,要实现氮这一主要营养元素的平衡,粮食亩产只能达到100公斤。这与现代农业能够达到的亩产400公斤相去甚远”。
天然农业、传统农业的“粮食亩产只能达到100公斤”?笔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与1958年主流媒体把粮食亩产“吹”成几万、十几万斤刚好相反,但性质却同样恶劣,这就是,凭借话语权高度,用明显违背常识的数据误导公众、误导知识界、学术界,误导管理层和决策层。
作为研究者、学者,尤其是官方高级研究机构的学者,本不应该出现如此低级的常识性错误,但错误真实存在,笔者只能推测,部长先生要不就是学术无能无德(高高在上,既没有认真研究历史资料,又缺乏深入基层,深入田间地头的经历),要不就是学术堕落。若这篇“奇文”被当过知青、种过地的中央领导看见,少不了严厉斥责,一顿臭骂。因为这也太离谱。
首先,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存的基础就是天然农业、传统农业,其特点正是“使用人力和畜力、靠人畜粪肥和绿肥维持地力”,若真是“粮食亩产100公斤”,那怎么能够发展成为数亿人口的大国;1950—1980年,我国很少使用化肥、农药,若真是“粮食亩产100公斤”,那还不饿死大多数国人?
其次,国家统计局的历史数据完全不支持“粮食亩产100公斤”的结论。
1952年全国平均粮食亩产的确仅有88.1公斤/亩,但那是“全国平均”,即用全国粮食总产量与全国播种面积计算的平均值,而全国播种面积包括大量广种薄收的贫瘠土地。在一般农业区,若用“夏粮+秋粮”、“早稻+秋粮”计算全国年均粮食产量,则分别为148.1、235.9公斤/亩。而真正粮食主产区的年均粮食产量则远高于这个平均水平。(一般地说,夏粮主要包括小麦、早稻,秋粮主要包括玉米、大豆、一季稻、中稻和晚稻,但不同地区的组合不同。)
到1970年,全国范围内仍然基本满足“人力和畜力、耕地不休耕和轮作、靠人畜粪肥和绿肥维持地力”的条件,与1952相比最大的改进就是,许多地方兴修水利地改田,该年全国平均粮食亩产为134.1公斤/亩,而由“夏粮+秋粮”、“早稻+秋粮”计算的全国平均粮食产量分别为218.2、384.5公斤/亩。
第三,在那些自然条件特别优越的地区,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单位面积产量远高于一般粮食主产区。比如,1983年全国农村全面实行“承包制”的当年,笔者的顶头上司(水电厂书记)回家收稻谷,应我的要求,他专门划了1亩田测算产量,结果是当场过秤超过1500公斤(湿谷),折算成黄谷(干谷)1200公斤/亩。1970年代,当地小麦亩产在400~500公斤/亩,而年均粮食亩产一般都能够达到甚至超过1500公斤/亩(当地小春种小麦,大春种水稻)。1980年前后,当地已经开始使用“土化肥”工业氨水增加氮营养,但农药用量极少。笔者在当地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并经常深入农村。当地人均土地仅有几分地,要在这么少的土地上养活一大家人,农民只能将精耕细作做到极至,再加上气候条件优越,所以单产在全国“拔尖”。据说,陈永贵当副总理时,不相信当地小麦产量过千斤,曾派人私访,并最终确认。
第四,因为30多年来(尤其是最近20年)大量使用化肥、农药,耕地已经普遍被“毒化”。尽管如此,若果断摒弃蒋高明所说的“六大害”(即化肥、杀虫剂、除草剂、激素、农膜和转基因),耕地也会逐渐“脱毒”并恢复活力,回归绿色、生态。
2006年7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蒋高明研究员,在完成了一系列绿色生态种植技术的理论论证以后,去山东平邑县蒋家庄村租下了40亩全村最差的耕地,取名“弘毅生态农场”,开始了他的生态农业试验。他带领一批研究生,经过5年艰苦努力,终于取得了丰硕成果。摒弃“六大害”以后的耕地,通过一系列生态技术措施越种越肥;弘毅生态农场单季产量小麦480.5公斤/亩,玉米547.9公斤/亩,年单位粮食产量达到1吨/亩,这与当地使用化肥农药耕种的单产水平相当。
2014年初,笔者与回国考察的熊航博士结伴考察四川农村,发现简阳的双河村已经实现了全面生态种植,包括水稻全部生态种植和全村全部农作物品种生态种植。该村从2010年开始,在镇农技干部和村干部的带领下,借助省农科院的水稻生态种植技术,从生态水稻种植入手,创造性地革新了绿色生态种植技术,并在全村阶梯式全面推进生态种植。仅仅3年时间,该村的绿色生态种植就覆盖了全村全部农作物品种(包括水稻、油菜、小麦、玉米、红薯、大豆、小杂粮、多种蔬菜和水果等等)和半数以上耕地。目前,该村实行生态种植的耕地全部停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激素,其它耕地的农药使用量减少70%以上;绝大多数村民的家禽家畜也完全拒绝激素饲料,其饲养周期都在1年左右,因此,该村农产品已经成为附近地区城镇居民购买绿色生态食品的首选。
现场考察时,令笔者感到意外的是,双河村第1年的生态水稻种植并没有大幅减产,秋收测产显示,生态种植的杂交稻平均亩量约450公斤/亩,比使用化肥农药的情况每亩仅减产10%(约50公斤左右)。到第3年,生态种植的杂交稻(农民不可以自留种)单产提高到520~530公斤/亩,常规稻(农民可以自留种,但产量稍低)的平均产量也有450公斤/亩(2015年秋收,该村部分试种并提前收割的常规稻单产高达682.1公斤/亩)。这显示,绿色生态种植已经不输于当地使用化肥农药的单产水平。
由此可见,部长先生关于传统农业“粮食亩产只能达到100公斤”的见解是何其之谬。
4、“绿起来”的农业是“伪绿色农业”
部长先生说,“现在我们所追求的绿色农业,本质上是以科学技术为支撑、以现代投入品为基础的集约农业”。这里作为“基础”的“现代投入品”不外乎就是化肥、杀虫剂、除草剂、激素、抗生素、农膜和转基因的代名词。因为,离开这些有毒有害玩意儿,“现代集约农业”就玩不转了。
例如,“现代集约农业”在种植业主要表现为“规模化种植”和“大棚种植”。对于前者,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必不可少,对于后者还必须加上激素和农膜两个要素。除此之外,在其它非集约的“现代农业”中,上述五大生产要素也已经渗透全国,甚至在那些人烟稀少的偏远山区,农民都已经在使用除草剂。
近两年,笔者给受训官员、乡镇干部和村干部讲课,问他们说,“有人主张全部停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和激素,你认为这可能吗?”在所有的培训班上,所有人(其中就有一线的农民)都异口同声地说,“这不可能!”由此可见,“现代农业”的“四大害”已经深入中国农业的“骨髓”。
但严重的问题在于,这“四大害”污染再加上“现代养殖业”的激素和抗生素污染(加在一起构成后文所说的“五大害”,包括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动植物激素、抗生素)已经在全国形成了严峻的局面:“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数量比城市或工业点源污染更加庞大,一些地方的农业源污染物指标甚至超过工业和城镇生活污染之和”。
这种局面对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在笔者所在城市,原来用作居民饮用水源的河流虽然没有遭受城市和工业污染,但却因为农业和乡村的“面源污染”(主要是“五大害”漫山遍野的污染),沦为实质上的Ⅳ类水而不能饮用。地方官员只好另找水源,并将水源地附近村民悉数迁移。
在养殖业方面,“现代集约农业”生产的激素鸡鸭1个月左右上市,激素生猪3、4个月出栏,而14亿张嘴已经离不开这些“激素+抗生素”喂养的家禽家畜。虽然许多农民留给自家食用的家禽家畜都拒绝激素饲料,并喂养1年以上才宰杀上餐桌,但如果全国都采用这样的生态养殖,那全国的肉类供求立即崩盘,绝大多数人口将无肉可食。
在14亿人口这个基本国情下,若部长先生一定要在“现代集约农业”上有所作为,那只能在有毒有害物质的“残留标准”上做点文章。如他所说“加快制订完善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使用的标准和技术规范体系”,别让瓜果打太多的“膨大素”,别让刚打农药的瓜果蔬菜上市害人。
其实,那些所谓的“技术规范”往往也只存在于纸面上,在农业一线有多少农民会理会这些技术官僚想当然的东西?更重要的是,现在耕地已经中毒很深,环境已经严重失衡,土壤和农作物对于“四大害”的依赖已经像“吸毒”一样形成恶性循环11,少用“四大害”往往意味着减产。本来仅有微利的农民会为了你的食品安全而甘心亏本?
部长先生在此的基本错误在于,将“现代农业”、“现代集约农业”伪装成“绿色农业”,从而模糊了两者的根本界线。
目前,在全面生态种植的双河村,以“生物多样性”原则为中心的一系列防病治虫措施和“取之于地还于地”理念指导下“以地养地”的一系列传统耕作技术已经深入人心。
“生物多样性”,这意味着要尽量做到农作物品种的合理搭配,坚决杜绝单一品种的大面积种植;要尽量保留田间地头的各种杂草(在双河村,高度超过农作物并遮光的杂草才会被除掉);还要给所谓的“害虫”(它们本来就是大自然的“合法”居民)留一块“蛋糕”,允许它们繁衍生息,以维持生物物种平衡,避免其“独大”为害。
“以地养地”的一系列做法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的农耕经验,它包含了现代农业科技论证了的一切营养元素“取之于地还于地”的理论精髓。
在该村现场座谈会上,笔者专门就“生态种植会不会使耕地肥力没有后劲”的问题与农技干部、村干部和村民进行了探讨,最后的结论是,该村生态种植的一系列“以地养地”措施只会使耕地越种越肥,而不是相反。其实,“弘毅生态农场”的试验也支持这一结论。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在传统农业地区,我们祖先几千年采用传统耕作方法后留给我们的都是非常肥沃的耕地。不像现世我辈,极有可能会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片被“五大害”毒化的贫瘠土地。实际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例如,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什么庄稼都种不活”的土地,有农民“深耕1米”,想埋掉那些“有毒泥土”12。
土壤是农业赖以存在的基础,但“现代农业”对土壤的破坏史无前例。它一方面造成土壤肥力递减,使耕地越种越瘦弱,病虫害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造成土壤严重污染,例如,化肥农药摧毁了土壤的微生物系统,导致土壤沙化或板结,同时,化肥农药都含有相当多的重金属,这是土壤重金属污染更为普遍的来源。
部长先生前面所说的“要实现氮这一主要营养元素的平衡”无非是说“保持肥力,持续耕种不减产”。而绿色生态种植一线的农民其实早已解决了这一问题。相反,部长先生所推崇的“现代农业”以“六大害”(“五大害”加上农膜)为生产要素,本质上是掠夺土地肥力,对土地“竭泽而渔”,最终一定会“失衡”并崩溃。
5、对农业发展方向的误读
曾经养活了数亿中国人的传统农业、绿色生态农业,如今何以嬗变为生产有毒有害农产品并严重污染环境的“现代农业”?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10多亿人口的吃饭压力,迫使我国牺牲农产品品质而追求产量。由于错误的人口政策,1982年,我国总人口超过10亿。“1980年以后的30年里,我国总人口净增35.9%,绝对增量3.5亿人。为了解决这3.5亿新增人口的吃饭问题,我们不得不让13.4亿人口一起去大量‘消费’化肥、农药、激素、抗生素和二恶英毒素。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人口现实!”13
第二,作为改革开放开局受益的农业领域,在“承包责任制”以后便没有什么值得圈点的实质性制度进步。在这种背景下,非农领域市场化改革的相当一部分成本被转嫁给了农业领域。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我国长期实行“低成本扩张战略”。该“战略”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维持基本生活资料低成本,支持“中国式”资源和劳动力廉价出口。绝大多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迫于生计,选择外出打工,但数亿农民工却仅有微薄的“裸工资”,而长期缺乏养老、医疗和失业三大保险。另一方面,因为数亿青壮年劳动力“出走”,作为民族生存基础的农业竟然主要由留守老人和少量中年妇女支撑局面(笔者2014年在四川农村考察,很难见到青壮年农民)。因为缺乏劳动力,这些老人和妇女种地无力使用传统农家肥,而被迫选择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和激素。明知道喷洒农药会使自己得病甚至患癌症,但农民无可奈何。
这种局面直接造成了四个问题:一是连农民自己吃的粮食和蔬菜也要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否则便会大幅减产。二是农民为了增收,越来越多地放弃粮食生产,转而生产尚有价格优势的蔬菜水果,甚至花卉、树苗。读者去查阅一下那些农民增收的诸多典型个案,一定很难见到粮食种植(除非是规模化种粮)。三是我国粮食生产的重心逐渐北移,缺水的北方,甚至内蒙古,因为尚有大片土地便成为新的粮食主产区,但大量抽取地下水种粮绝对不可持续。相反,历来鱼米之乡的江南地区却逐渐远离粮食生产。例如,在前文提到的全国小麦单产最高的那些乡镇,如今连一粒小麦也不生产。四是为了避免过度粮食进口,有关部门近些年越来越多地支持粮食的规模化种植,甚至支持非农产业资本下乡,但这种农业模式在两方面表现出很大弊端。一方面,规模化种植只能依靠“现代农业”的“六大害”,另一方面,非农产业资本的挤压和规模化种植对小农具有“挤出效应”,这对数亿农民来说,可能有灾难性的后果14。
可见,仍然牺牲农业、农民去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迟滞农业体制改革,导致农民的基本权益缺乏制度保障,其后果就是农业凋敝,农民另谋出路,而农业的发展方向则被导向由高度依赖“六大害”的所谓“现代农业”。
第三,农业是市场经济中外部效应最为显着的部门之一,世界主要国家,尤其是已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都没有将农业完全交给市场,任由其全面规模化经营,相反,他们都是在“充分肯定中小农户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通过帮助农民建立合作社,并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去实现农业产业化,实现小农业与现代化大市场的对接”15。据李昌平考证,为了保护小农,免于被非农产业资本挤压而破产,“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限制大资本下乡,大约经历了数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16。
部长先生主张的“现代农业”离不开“六大害”农业生产要素,这与绿色生态农业有本质区别。笔者在考察双河村全面生态种植的报告中曾经指出了这一关系农业发展方向的本质区别:“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在农业生产方式上,人类很可能正走在一段弯路上。这主要表现为,人们抛弃了对环境友好、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且成本低廉的绿色生态的传统农业,而代之以由‘绿色革命’所形成的‘现代农业’(或曰‘石油农业’)。这种所谓‘绿色革命’以工业化为支撑,以大量技术、资金和物质投入为基础,实际上就是越来越多地依靠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激素、除草剂、农膜和转基因手段,维持所谓‘高产、高效’农业,其结果,一方面造成农产品品质下降、安全性降低,另一方面,又使得环境污染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持续恶化的趋势。”17
对于后一恶果,笔者将在《水污染才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评〈2014环境公报〉水污染形势研判》一文中详述。(该文即将在期刊发表,为保证其“首发”,这里只能推迟发表。)
6、绿色生态种植的真正意义
笔者在考察中看到,双河村村民从全面生态种植中受益颇多。一是农产品品质大幅提升,村民吃上了绿色生态健康的食品。二是一系列绿色生态剩余农产品都卖出了好价钱,例如常规稻大米的价格提升了4倍。三是村民的种植劳动是健康的,他们不再因为喷洒农药而受到毒害,这明显减少了患病的概率。四是环境明显改善,水质、空气逐渐好转,昆虫种群逐渐恢复平衡,虫害明显减轻。五是全面生态种植大大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指数”。笔者与该村村民交谈,他们认为自己吃得比城里人健康,再加上水好、空气好,身体更健康,其“自豪感”油然而生。笔者看到,该村村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大增,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其面貌焕然一新。18
显而易见的是,双河村全面生态种植的经验不可能在全国推广,因为,前面说过,在14亿人口大国,全面绿色生态种植养殖“恐怕连半数国人也养活不了”。仍以双河村为例。该村500余户,1700多人,半数以上外出打工;耕地面积约1980亩,人均耕地1.15亩,其中,水田300亩,人均不足0.2亩。粗略估算,由于人多地少,在全面绿色生态种植的条件下,该村目前能够提供给社会的剩余农产品不会超过20%。
在上述前提下,目前绿色生态种植的现实意义只能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有条件(主要是远离城市、工业区且没有外来河流污染)的农村地区,尤其是生态环境较好的山区,可以有组织地实施全面绿色生态种植,这可以让村民、山民过上绿色生态健康的生活。
由于生态种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生态农产品又有更高的价格,因而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这可以吸引打工“游子”回村就业,“空巢”家庭有望减少,这些农村地区的衰败有望被遏制。
但是,不能期望绿色生态种植能够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主要原因也是人多地少,人均绿色生态农业资源太少的缘故。不过,它能够在有限地区恢复农民山民低成本、绿色生态的传统生活方式,这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笔者曾在双河村考察报告的结语中写道:我们许多人,尤其是一些地方官员(也包括不少学者),就是看不得农民、牧民、山民的低成本、绿色、生态的传统生活方式,总认为他们落后、保守、不开放;总想把这些低成本传统生活方式“赶尽杀绝”,以便把他们纳入自己的所谓“现代化”、“城镇化”的“宏伟规划蓝图”之中。殊不知,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这是轻视人类丰富的创造力,无视人类文明多元化,并明显带有某种非常恶劣却又难以言说的偏执和狭隘(其背后往往暗藏私利);他们骨子里把“美国式现代化”看成是发展方向,把高楼林立看成是“现代化”的标志,把汽车拥堵看成“现代生活方式”,其结果就是,“我国资源早已严重超载、透支,环境污染触目惊心且已经临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边缘”。19
第二,全面实施绿色生态种植的农村地区能够有效恢复生态环境,增加我国环境后备容量。
笔者在《人口困局》第8章第2节详细论述了我国“先污染后治理”愿望落空的严峻现实,在随后发表于《中国改革》杂志的文章中,笔者进一步将这一严峻现实概括为20:由于“人口高位运行”和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目前已经出现城乡全面、立体污染的严重局面,这意味着,我国环境的后备容量已所剩无几,我国环境治理事实上已经缺乏“战略纵深”,缺乏“战略回旋余地”。在这种局面下,环境治理最终是赶不上环境污染速度的,因此,我国的环境只能长期维持“局部有所改善,整体在恶化”的局面。
但是,如果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尤其是绿色山区,有组织地实施全面绿色生态种植,那就可望在许多流域(尤其是小流域)的源头地区恢复绿色生态环境,这无疑会增加我国环境的后备容量,对于遏制严重水污染无疑会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实际上,近些年,许多地方政府出台的水源地保护法规,都明确规定,禁用农药、化肥、激素。例如,《成都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21规定,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禁止使用农药和化肥,禁止畜禽养殖(等于禁激素和抗生素)。
第三,由于人多地少且环境严重污染,绿色生态农业资源已经非常有限,所以绿色生态种植所能够提供的剩余农产品非常有限。从全社会来看,除了从事绿色生态种植的农民以外,只有极少数城镇人口能够从中受益。
部长先生也知道绿色生态农产品的稀缺性,他说,“不用化肥和农药的种植业,不喂饲料和添加剂的养殖业可以少量存在,但难以成为现代农业的主流”。他的前一分句是成立的,但后一分句存在“语病”。绿色生态种植不是“难以成为现代农业的主流”,而是与“现代农业”完全不相容。
由于绿色生态农产品稀缺且价高,于是有些人便想利用一些“现代农业”生产手段扩大绿色生态种植,以便增加其剩余农产品,比如,使用机械化耕种,通过公司化、规模化经营,等等。但是,笔者非常遗憾地告诉诸位,这种深深打上了“现代农业”烙印的惯性思维与绿色生态种植理念格格不入。
虽然,绿色生态种植并不排斥农业机械(一般应小型化),但拒绝大规模的机械化耕种方式;绿色生态种植也需要资金投入,需要金融扶持,但是拒绝非农产业资本下乡,拒绝侵占农民利益的公司化(如“公司+农户”),拒绝排挤小农并力图消灭农业家庭经营的土地规模经营。
绿色生态种植所遵循的“生物多样性”和“取之于地还于地”基本原则与“现代农业”毫不相容。从双河村的实践来看,“生物多样性”拒绝单一品种大面积种植,以防治单一病虫害大面积爆发,同时,“生物多样性”还要求保持农作物与环境的平衡。后者包括,杂草之间的平衡,以避免单一杂草独大为害;昆虫之间的平衡,以避免单一昆虫独大为害;杂草与昆虫之间的平衡,以便利用杂草抑制昆虫成灾(当地一位承包果林的前小学老师给我们描述了他近几年“利用杂草抑制昆虫成灾”的正反试验过程)。“取之于地还于地”的原则包括使用传统农家肥(包括堆肥、秸秆还田、种植绿肥等)和“以地养地”的一系列措施。
绿色生态种植的上述基本原则和要求,是“现代农业”及其大型机械化耕种、公司化、规模化经营完全无法实现的。从根本上说,“现代农业”只能依靠“六大害”支撑,而与绿色生态种植无缘。
推而论之,在我国“人口高位运行”结束之前,绿色生态种养殖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绿色生态农产品给城镇居民。这也就是说,对于14亿中国人来说,真正的绿色生态食品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品”。与一般奢侈品不同的是,这种“奢侈品”主要由从事绿色生态食品生产的农民享用。
第四,对于绝大多数城镇人口来说,绿色生态种养殖和绿色生态食品可以作为一种美好的理想,并寄希望于遥远的未来。人还是需要希望的。至于这些人口的现实食品供应,那恐怕只能依靠“现代农业”提供浸润“六大害”的农产品。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当然,从理论上说,在“现代农业”和绿色生态种植之间还有一条“中间道路”,这就是增加农家肥,并采取生物治虫防病措施,减少“四大害”使用量以改善农产品品质。但这条“中间道路”荆棘丛生,其困难程度甚至超过了纯正的绿色生态种植。一则,增加农家肥需要增加农业劳动力,需要外出打工的游子回村,这需要调整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利益关系,需要调整一系列三农政策,这难乎其难。二则,采取生物治虫防病措施往往需要与生态环境形成“互动”,本质上需要生态环境的改善,但这与我国环境“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大趋势相悖。三则,“中间道路”本质上与官方提倡的城镇化、土地规模经营相左,这更增加了付诸实施的难度。
因此,好像与许多重大事情一样,“中间道路”往往只存在于理论与理想中,而与实践和现实无缘。